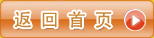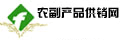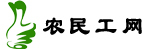清凉山
山西之清凉山海拔三千余米,范围二百五十余里,山高林密,寺院林立,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。南京之清凉山,无论海拔、范围均不足以与之媲美,但因其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这座并不雄伟高峻的钟山余脉,千百年来亦为人称道。
南京之清凉山位于城西汉中门内,原名石头山,因历史上曾依山建城又名石城山;山中有清凉寺,故又称清凉山。清凉寺原为杨吴顺义元年(921)所建之兴教寺。南唐昇元元年(937)改为清凉道场,为后主李煜诵经拜佛之处。寺后建有避暑宫德庆堂,寺傍有掘于保大三年(945)之保大井。宋太平兴国五年(980),清凉广慧寺从幕府山迁来此地;淳祐十二年(1252)在山巅建有翠微亭,又名暑风亭。明建文四年(1402)重建,改称清凉寺。太平天国军兴,寺庙毁于战火。清末重建,但规模大不如前。抗战时期又遭日军破坏。建国后多次修葺,乃成为南京胜景之一。
山中文化蕴涵极为丰厚,如南唐中主李璟书写的《祭悟空禅师》碑文,后主李煜书写的“德庆堂”榜石刻,但存世不过二百年左右;宋代诗人陆游于乾道六年(1170)七月游此山时已未曾见到原物,仅从清凉寺宝余禅师处得到墨本,陆游在其所作《入蜀记》中叙及此事。又如宋时福建福清人郑侠曾于山中读书,他曾绘有“流民图”献给神宗而遭贬,离任时身无长物,仅存一拂,后人钦其清节,于其读书处建一拂祠以祭,其处“地甚幽深,树木参错,深秋时枫红竹绿,终日无一人至者,所谓城市而山林也”(陈诒绂《石城山志》)。其祠今已不存,但“城市山林”之美誉一直为人称道。再如,明代都御史、湖北黄安人耿定向曾主讲山中之崇正书院,南京有名的焦状元(竑)即其弟子。由明入清的画家龚贤,为“金陵八家”之首,曾结庐于半亩园,并绘有一僧执帚扫叶图悬于楼上,因而“扫叶楼”乃闻名于世。崇正书院与扫叶楼业已修复,希望能为大众共享。清初著名讽刺小说家吴敬梓曾多次来游此山,在其所著的不朽名作《儒林外史》中曾描写此山及附近之乌龙潭的景致、人物,也无一遗存。据《盋山志》所记吴敬梓“殁葬清凉山麓”,但其墓也无处可寻。
至于山之左近,尚有惜阴书院,当年一些学者名流如俞正燮、胡培翚、冯桂芬等都曾执教于此。方苞之教忠祠也建于山麓。山前之乌龙潭,有颜真卿之放生池。明末清初有名的藏书家丁雄飞之藏书处“心太平庵”亦建在乌龙潭。清初极擅中西之学的周榘之“幔亭读书处”亦在此处。《海国图志》作者、湖南人魏源之“小卷阿”别墅亦建在附近。
南京清凉山虽不如山西清凉山为佛教圣地,但也是禅宗南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法眼宗”的发祥地。五代僧人文益(885—958),俗姓鲁,原为浙江余杭人,七岁剃发,二十岁受戒,于宁波习律,去福州、漳州参禅,晚年受中主李璟敬重迎至南京弘法,先居报恩院,后移清凉寺。为救“禅宗”空疏之敝,他主张多读书以求“圆融”悟禅,圆寂后被谥为“大法眼禅师”,乃成为法眼宗的开山祖师。此宗在宋初一度盛行,后渐衰落。但其再传弟子延寿曾收有三十六位高丽僧人学法,此宗乃传入朝鲜。
山中小九华寺香火很盛,尤其在农历七月盂兰盆会前后。据《金陵岁时记·地藏蓬》云,地藏菩萨“俗家姓金,名乔觉”,在“唐高宗永徽四年”于安徽九华山“端坐山头,凡七十五载,元(玄)宗开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夜成道,在世九十有九。肃宗至德二年七月三十日,显圣金陵之清凉山,俗名曰小九华”。又据《金陵待征录》,该“寺据山巅,殿之四面各塑佛相,异于他寺佛座之制。……中奉地藏画相,旁奉十殿阎罗画相”。南京大街小巷所举办之盂兰盆会,最后一天必将供品送至清凉山小九华寺地藏王相前,诵经礼佛方始结束。正因为清凉山中有如此繁盛的佛事活动,明人葛寅亮在《金陵梵刹志》中将“清凉寺”列入三十二“中刹”之列,该书“大刹”仅有灵谷、天界、报恩三寺,其后有五“次大刹”,再后就是“中刹”,至于“小刹”则有一百二十八,另有无名“小刹”一百余所。由此亦可见清凉寺在南京梵刹中之地位。
综而言之,在历史上清凉山周围既有书院又有藏书楼,不少学者文人、高僧大德卜居于此,或讲学或著述或弘法,文化气氛十分浓郁,积淀的文化底蕴也极其丰厚。如今鼓楼区高校之多,人才之众,文风之盛也为全市之冠,由来久矣。
二
正因为清凉山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,不仅历来南京史志中有所叙及,如民国年间的《首都志》,为先师王焕镳所编纂,在卷四“山陵下”之“城西诸山”中亦有“石头山”之介绍。但一般志书限于体例,大都叙述简明,而有关清凉山之专志则可详说。目前所知有关清凉山之专志有四种,即丁雄飞之《清凉山志》、周榘之《清凉小志》、顾云之《盋山志》和陈诒绂之《石城山志》。可惜丁、周二氏之作今已不得见。
丁雄飞,明末清初江浦(南京)人,其父丁明登喜藏书,雄飞除继承乃父藏书外,又能亲自搜罗收购,藏于乌龙潭上之“心太平庵”中。他与南京另一位藏书家“千顷斋”主人黄虞稷为忘年交,还结成相互借阅图书、探讨学问的“古欢社”,立有为后人称道的社约,有“借书不得逾半月”、“还书不得托人转致”等条款。丁氏生平著述甚丰,有关南京的志书也有多种,有《乌龙潭志》、《清凉山志》、《珍珠泉志》等,可惜大都散佚不可见。
周榘,上元(今南京)人,住在乌龙潭附近,字幔亭,所居有额,题有“周幔亭先生读书处”。他不但善诗工书,而且潜心于科学技术,“能以拳木造天球,以尺绡画江河万里”,还懂得“华严字母法”,被时人称为“振奇人”,著作甚丰,有《阙里小志》、《清凉山志》等,但也散佚。《金陵通传》、《盋山志》均有其小传。《金陵待征录》“卷之十志物”中有“清凉散”条目,云:“周榘撰,未刊稿本也,一名《清凉小志》。”在称引周志序言数语后,金鳌又云:“此书不久必佚,录之俾人思幔亭笔墨。”在该书“卷一之志地”之“清凉山”条目中,金氏又云:“所采多据周幔亭榘《小志》,志无刻本。”《待征录》金鳌自序作于“甲辰二月”,即道光二十四年(1844),可见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前,周志尚存,今已不得见。
今日可以见及书者有顾云之《盋山志》。顾氏生于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卒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南京本土人。同光年间,全椒薛慰农(字时雨)主讲惜阴书院,顾云从其学,并与同门共建“薛庐”于乌龙潭畔,同“居山中数载”研讨学问。时雨乃命众弟子“相与志之”,诸同门或“物故”或“有四方之役”而不能为,顾云乃秉承师命执笔成书(《盋山志·例言》),今有盋山精舍光绪九年(1883)刊本。该志分五门八卷:形胜、祠庙、园墅、人物(上、中、下)、艺文(上、下),所志范围即清凉山四周。所谓“盋山者,又石头山之一干,而支于钟山焉。(《盋山志·引》)”
笔者曾多次检阅顾志,乃因薛时雨与吴敬梓同为全椒人,特别是薛氏曾“笺注”过《儒林外史》,并曾“集资刊行”(见《全椒志·流寓·金和传》),可惜薛时雨注本经多方寻求亦未得见,上世纪七十年初,笔者曾去全椒寻到薛氏后人,为一中学教师,对其先人事迹也不甚了了。因为多次翻检,颇觉顾氏下笔慎重,力求“事必有征”,如有异说则予列出,如卷四“吴敬梓”条,记吴敬梓“殁葬清凉山麓,或曰在凤台门”,二说并存。关于吴敬梓“殁葬”清凉山一事,数年前笔者应邀与几位热心人踏遍清凉山头,未曾寻到任何踪迹;近年亦有吴敬梓后人自全椒来寻,也无结果。但有一位在清凉山公园工作多年的同志一再电告我,他曾亲见吴敬梓墓碑,但却又不肯出示实证。既无实证,顾志又列出另一说,此事只能存疑,待诸来日有新的发现再做结论。不过,从这一点亦可见顾云之慎审态度。
顾志刊刻三十余年后又有陈诒绂之《石城山志》出。此志有李详作于“戊午端阳后一日”及可园老人作于“丁巳冬至日”两篇序言。“丁巳”为1917年,“戊午”为1918年。李详(1859—1931)字审言,是扬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,曾任过江楚编译局总纂、东南大学教授、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等,生平著述甚丰,其后人辑录有《李审言文集》行世。可园即陈作霖(1837—1920),为陈诒绂之父,是南京著名的学者,于乡邦文献的搜集、编纂贡献良多,最著者如《金陵通传》、《金陵通纪》、《金陵琐志》等;乃子诒绂“学步邯郸”,除撰有《钟南淮北区域志》外,又“以顾氏《盋山志》为张本,略者使详,散者使整”(《石城山志·引言》)。在乃父指导下成《石城山志》一书,可园老人在《序》中明言“父述子作,仍为一家之言”。但此志实为补顾志而为,以一帧“石城诸山图”冠于卷首,其后分“山北路”、“山南路”、“山东路”分述,全书不过数千字而已。由此观之,有关清凉山之志志,当以顾氏《盋山志》最为详备,也最受学人之重视。顾、陈二志之后,近百年无有续之者。
三
苏君克勤近日持其所著《南京清凉山》书稿来舍间,请笔者为之作序。昔贤有言“人之患”不仅在“好为人师”,亦在“好为人作序”。何其不幸,不佞二患兼有,但“为人师”乃由组织分派,不能自主,以致罹此“患”整整五十年;而“为人作序”,虽一再声明不作此勾当,但也有不得不为之者,也可说是自己“贾祸”,而不得不为之者有两类著作:一是弟子的著作,二是有关桑梓的著作。第一类的著作较多,大多是由学位论文发展而成专著,弟子求序,忝为导师,责无旁贷,诸如胡金望教授之《阮大铖研究》、李延年教授之《<歧路灯>研究》、吴秀华教授之《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》、高小康教授之《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》、徐定宝教授之《凌濛初研究》、方晓红教授之《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》、乔光辉教授之《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》、吴波教授之《<阅微草堂笔记>研究》、周玉波编审之《明代民歌研究》、张则桐副教授之《张岱探稿》,等等,他们的专著分别由人民出版社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江苏古籍出版社、中州古籍出版社和黄山书社等出版社出版。我所写的序言还有数篇先行在《长江学术》、《中国文学研究》、《东南大学学报》、《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,无论出版社或刊物的编辑对不佞所写的序言均无异议,但也有一位自以为是的编辑坚持序只能评书,不能言及作者及有关内容,将“序”与“书评”等同起来。这种见解,与鲁迅所言“我以为倘要论文,最好是顾及全篇,并且顾及作者全人,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,这才较为确凿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题未定草》)的正确主张完全相背,只能置之不理。
对于第二类著作即有关桑梓的学术著作,有请不佞作序者,也勉力为之,乃因“惟桑与梓,必恭敬止。”(《诗·小雅》),乡邦之情,人皆有之。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,可园老人曾孙、陈诒绂之孙陈鸣钟先生拟将历代南京学人事迹汇为一编,以理清南京学术发展的脉络。鸣钟先生的志愿得到南京市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,南京市社联何开庸、邬醒倩两位同志来舍间相约,特别是邬醒倩同志多次前来交谈,约定去淮海路鸣钟先生府上(可园老人之可园却在安品街20号)研究相关事宜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先行编出《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》。但鸣钟先生未及见其书出版已归道山,确为憾事。不过,南京市有关部门仍组织有关学者继续鸣钟先生未竟事业。2002年春,南京社会科学院邀约一些学者座谈,拟继续编写南京学术人物传,周直院长一再请我承担“明代”卷的主编,当时因公私鞅掌,不能兼顾,乃推荐沈君新林承担。清样出来后,周院长仍请我任主编,我因未有贡献,不能挂名,退而请我为序,乃因“事涉桑梓,敢不命笔”(序)。此序也先行在刊物上发表。
苏君之《南京清凉山》一书同样引发笔者桑梓之情,尤其是笔者于1964年从江苏师范学院(今改为苏州大学)调回南京工作以来,一直住在清凉山附近,至今已整整四十五年,长年在山中散步,有着浓厚的清凉情结,上述为诸弟子著作所写序言,大都标明“作于清凉山下”;自己出版的著作中,前言后记中注明“作于清凉山下”者也近二十部。论文自选集即题名《清凉文集》,批评的《儒林外史》也名之曰《清凉布褐批评<儒林外史>》,还写过三数篇有关清凉山的散文随笔。苏君前来约请为序,又岂能拒之?苏君书稿中举凡清凉山之形胜、楼馆、园墅、寺观、人文……均有所叙及,无异是顾、陈二志之后的新时代的一部《清凉山志》。虽然对该书的具体评价要在出版后由读者和专家作出,但以苏君著作之丰、用力之勤,可以觇知此书必可在弘扬清凉山文化底蕴方面作出贡献。
特别要说明的是,苏君本为中州人氏,除撰写有《彭雪枫全传》(曾获河南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)、《项羽虞姬传奇》等作品外,更关注南京的文化事业,多年辛勤搜集、整理、写成《南京名人旧居》一厚册,令人刮目。而苏君的这些成绩又与鼓楼区的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。犹记2007年7月间,该区建设局徐副局长与文化局张局长通过我校组织部找到舍间,说奉沈区长之命前来探访,邀约我参加鼓楼区的文化事业活动,乃先后出席了有关乌龙潭和四望山文化建设两次座谈会,就是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得与苏君相识。2008年12月,市、区有关部门在崇正书院召开了“清凉山文化与南京”首届论坛,不佞也应邀出席。此会之后至今不过八、九个月,苏君即撰成《南京清凉山》一稿,可见苏君此作适应了市、区加强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,自有其意义。为此,乃应苏君之请,略写数语以为序。
相关资讯